|
 ! `0 k9 K7 T( c# l* L
! `0 k9 K7 T( c# l* L
. l+ f; @, l2 \* Y+ \- D) S
张贤亮自述:我也“饿死”过 文/张贤亮 原载于2012年新京报 1 K9 ]/ u5 O9 x6 r9 H: b" E7 m- J/ R
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当中经历过一次罕见的大饥馑,我那时候正在劳改农场。在劳改农场有一个好处,毕竟有定粮。那个时候的劳改犯人一个月的定粮是九斤粮食,这九斤粮食是带皮的原粮,那个时候用的还是小两,一斤是16两。而且你要知道,这里面还有苛扣啊,队长苛扣一点,厨师苛扣一点,到我们手里顶多只有7斤不到。你想,没有肉没有菜没有蛋,一天只有2两多原粮,你怎么活?而且长期如此,不是一天两天。把这2两多原粮磨成可以入嘴的所谓的饭,其实就是稀汤了。所以《我的菩提树》的英译本书名就叫做“Grass Soup”,“草汤”嘛。
& W' W* X) K$ U5 e6 z人在这样一种长期饥饿的状态下,就会引起极度的营养不良,因为营养不良,最显著的病症就是浮肿。 我也死过,所谓“死”是假死,我们现在讲就是休克,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。我的故事都有点黑色幽默,我倒下之后就有人把我送到太平间了。在太平间,我半夜又醒了。醒来之后我看到我周围的人全身赤裸,因为大饥荒年代什么都缺,死人身上的衣服都给扒掉了,寸布不留。我也是这样,大冬天的,那是1960年冬天,零下20度。但我活过来了,人求生的本能是很强的,因为有月亮照射,我依稀地看到门在哪儿,所以我就往门那儿爬,爬着我又晕过去了。第二天他们来收尸,推门推不动,因为我正好爬到门边上,顶在那儿了。于是他们就把门抬开了,因为是老式的门,可以抬起来的。他们一看,这个人昨天扔在那儿,怎么今天爬到门口来了?一摸我,还有点气,就把我送到劳改队的医院。恰好那个医生也是劳改犯,他在1957年的时候读过我的诗,挺同情我的。因为我身体太虚弱,要增加营养,他想了一个办法,让我吃乌鸡白凤丸,劳改队女性的药有多的。他就天天喂我这个玩意儿,一天喂好几颗,我就这么活过来了。 ; S5 Q1 P" Q- D2 u2 o! f
 % ~9 i% G* H" {
% ~9 i% G* H" {
▲1994年,宁夏镇北堡,“下海”后的张贤亮(左二)为海外客人讲解西部影视城的情况,1994年影视城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。
& [+ ]9 X; D- v; T' X3 J/ y m专访张贤亮:争论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采写/新京报记者 张弘 原载于2008年新京报
$ [4 q8 b# z$ ?0 t2 K U* t新京报:你1979年才被平反,1980年被调到宁夏文联当编辑,这时你的生活才开始安定并投入文学创作,当时,对社会形势的基本走向有怎样的判断? 张贤亮: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,那时才20岁。当时很不懂事,报纸、杂志上都说我错了,所以我真正认为是自己错了。后来被投入劳改队。一开始,我是真心地想洗心革面,改造自己。到了1960年的大饥饿,我就开始怀疑,不是我错了,而是政策错了,因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 新京报:依据什么? 张贤亮:我手头正好有《资本论》,它启发了我最基本的道理,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,就当时的生产力而言,我们不可能一步建成社会主义,更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。所以我就认为,当时左的政策,是必然行不通的,一定要改变。到了1979年我被平反以后,邓小平再次复出,“真理标准”的讨论展开,我据此判断,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,我觉得,新的时代来临了,这也不断促进我日后突破进取。 新京报:小说创作可谓一帆风顺,获得了很大成功,这使你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 张贤亮:应该说,我的处境从1979年平反,1980年调入宁夏文联开始,就有了变化。首先是结婚生子,其次摘去了帽子彻底恢复名誉。第三,写小说一炮走红。
W! O& W8 K5 B8 T$ \* y) \ X4 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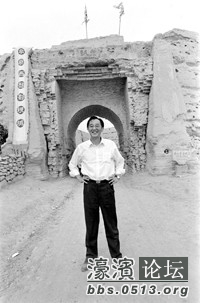
3 G$ o x ~+ ]! T9 O' a+ h0 n ▲1994年,张贤亮在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新京报: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(以下简称《男》)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“性禁区”的小说,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。 张贤亮:《男》是1985年发表的,之前,我已凭《灵与肉》、《肖尔布拉克》分别获得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收获》杂志刊出《男》之后,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当时我在美国,从美联社的电讯上知道了国内对我的批判。于是我去找中文报纸来看,有评论说,针对张贤亮的《男》,中国正在展开新一轮的思想整肃运动。这时,台湾当局下面有人给我打电话,让我留在美国,他们保证我的生活。只要我答应,他们马上给我一笔巨款。我当即回绝了。 回国以后,有关《男》的争论铺天盖地。坦率地说,我一篇都没有认真看,就是大致看看题目。我知道,无论是赞扬我的,还是批评我的,都会对我产生一定影响。 新京报:你那时就对自己的作品有充分的自信吗? 张贤亮:那时确实有。而且,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看,因为争论实在太多了,每个地方的报纸都有。一类就是批判,说我受资产阶级文学观的影响,骨子里面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;还有一类是纯赞扬的;中间一类承认我在文学上的成就,但是也有批判。应该说,争鸣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,反而更加提高了我的知名度。
: X; u7 \4 y. R+ V/ r; e! n% ?南通0 |  苏公网安备 32060202000307号 © 2001-2019 0513.org All Right Reserved.
苏公网安备 32060202000307号 © 2001-2019 0513.org All Right Reserved.